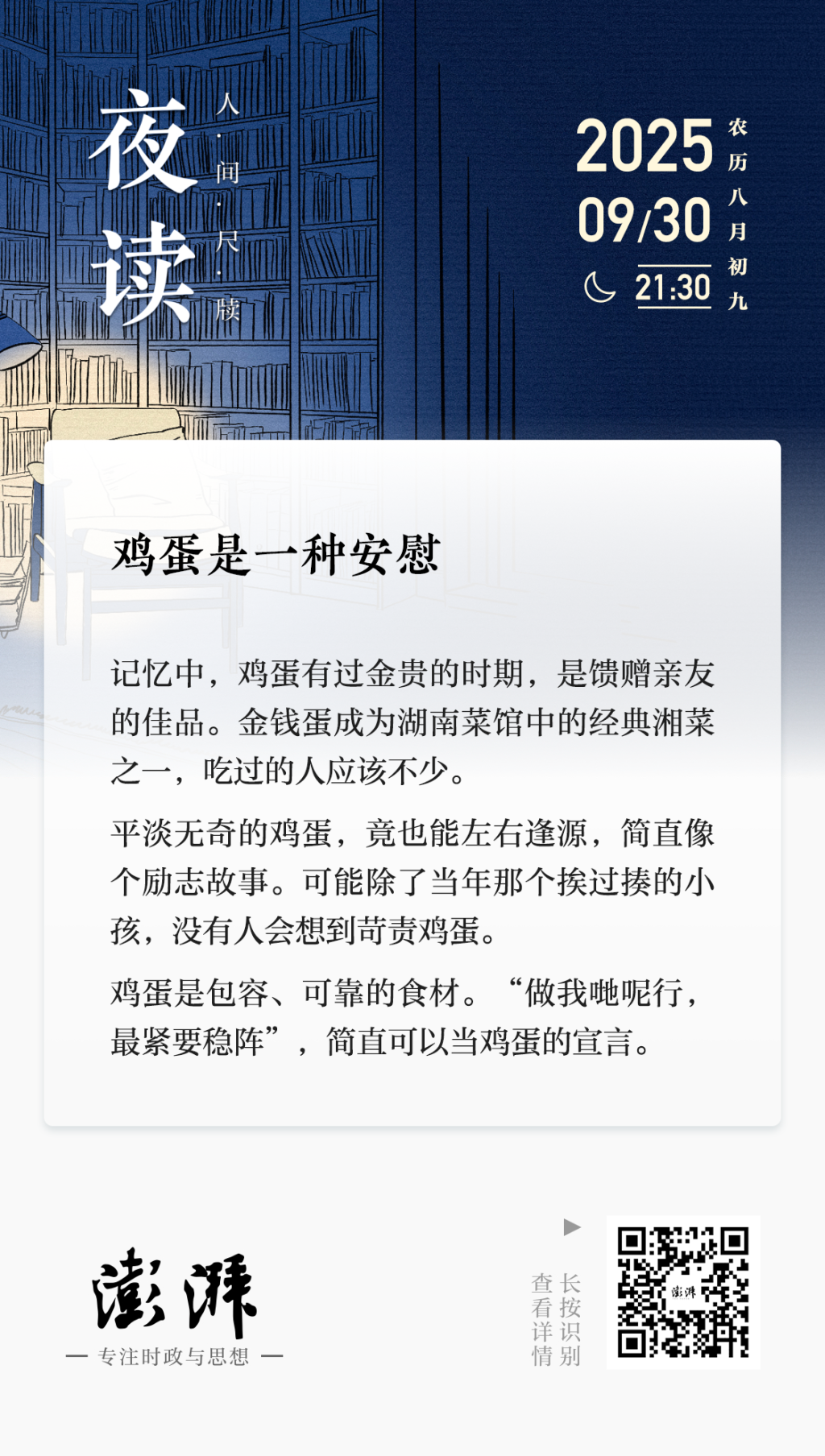幼年时,我性格倔强,常引得父亲动用家法,挨一顿打骂。哭累睡着后醒来,总会收到两个温热的煮鸡蛋作为安抚,递到我手中时温度适宜。我猜想,那份温暖或许与父亲责罚后偷偷抹去的泪水相仿。
在记忆里,鸡蛋曾有一段珍贵的岁月,是逢年过节赠送亲友的优选礼品。烹饪方法上,整只白煮蛋最能展现其高雅。但即便是作为重要的慰藉品,那两个煮鸡蛋也显得过于清淡,味道上难以有太大突破。倘若再挨一次打,我反倒更期待母亲为我烹制一道金钱蛋。
这道菜肴的起源已不可考,在鸡蛋供应不充裕的年代也不算家常菜。但不知何时起,它已成为各地湖南餐馆中的经典湘菜之一,品尝过的人应当不少。做法相对简单,将鸡蛋煮熟去壳,切片煎至两面金黄,再加入青红辣椒、豆豉、蒜苗或韭菜一同翻炒。
对于口味偏重的人来说,成片的鸡蛋仍不太下饭,口感类似油炸点心。反而是热油将部分散落的蛋黄炒得沙沙的,均匀裹在蔬菜上,香气诱人,能让人大口吃饭。
有些餐馆为保持外观,避免蛋黄过于松散,会将鸡蛋冷藏后去壳,切片高温快炸,或直接裹上生粉。人们为追求美食,不断钻研改进技艺,想想确实令人振奋。
我自己制作这道菜时,总觉得无论油炸还是裹粉,都不如小火慢煎来得香浓,因此仍沿用传统方法,但在其他方面常尝试创新。
一次在广州朋友家下厨,快出锅时,看到旁边有洗净的鲜绿薄荷,摘几片加入翻炒几下,焦香与清香交融,意外地和谐。几年后与朋友重逢,她说,你当年做的那道鸡蛋,真是让人回味无穷。
茴香上市的季节,我还试过用它替代其他配菜,同样获得好评。记忆中平淡的鸡蛋,竟能如此多变,简直像一则励志故事。
朋友有道拿手菜,也用鸡蛋做主料,叫赛螃蟹。将蛋白和蛋黄分开烹得嫩滑,加入蒸熟的鱼肉丝,以姜醋汁调味,味道鲜美可比新鲜螃蟹。简易版可不加鱼肉丝。只要有姜醋汁支撑,鸡蛋就能大变身。
我母亲有个更简单的版本。她有几个精心打理的陈年泡菜坛,泡菜水清澈香醇。将几颗鸡蛋打入碗中,加两三勺泡菜水,搅拌均匀后快速在热油中炒成糊状。这时鸡蛋形似柔和蟹粉,入口却带来酸爽微辣的刺激。历经长时间封存的泡菜水,在鸡蛋的辅助下,仿佛重获新生般欢快。浇在米饭上,我就能愉快地吃光。
我模仿母亲的泡菜坛后,也做过这道菜。但因泡菜水年份不足,或许因使用玻璃罐而非瓦坛,风味差很多。上次请朋友来家吃饭,最后做这道菜时,锅温过高,鸡蛋迅速凝固成块。端上桌时,我像个犯错的小学生。朋友们不知原菜应有的样子,从容地吃完了。
或许除了当年那个挨过打的孩子,没人会苛责鸡蛋。
毕竟它已是十分包容、可靠的食材。像我这种爱好烹饪的业余厨师,能用它捣鼓出几道菜;遇到高手,一颗普通鸡蛋也能变成米其林餐厅里精致的法式烤蛋盅。港剧中有句经典台词:做我们这一行,最重要的是稳妥,简直可作鸡蛋的宣言。
这样想来,鸡蛋本身就是一种安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