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编者按】
《天津工人:1900—1949》作为聚焦解放前天津工人生产生活的经典著作,通过海量口述史料与历史文献,系统呈现了劳动雇佣、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等多维生活场景。该书不仅还原了近代天津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阶层生存状态,更特别关注女工在工厂、家庭与社区中的多重社会角色。本文内容节选自该书,由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独家刊发。
作为城市移民群体的重要构成,天津工人阶层虽常面临就业不稳定的困境,却在频繁的职业流动中构建起独特的生活秩序。这种从乡村移植而来的社会网络,通过地缘与亲缘关系的维系,既强化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,也为工人们创造了重构社会关系的文化空间。他们的休闲方式与民俗活动,既是乡土记忆的活态传承,更是适应城市生存的文化策略。
在城乡文化交融过程中,工人群体既保持着传统底色,又主动拓展社会联结。"三不管"等娱乐区的兴起,使得外县曲艺成为新的文化消费选择;生存竞争中的冲突摩擦,并未导致社区纽带的断裂,反而通过共同的行为规范强化了群体认同。这种看似无序的生活状态,实则暗含着独特的社会运行逻辑。
市场和娱乐
尽管经济条件有限,逛市场仍是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每日的食品采购、钱庄兑钱等事务性活动,与流动摊贩的二手货交易共同构成市场生态。对于无力负担娱乐消费的工人而言,市场既是"看热闹"的免费休闲场所,也是观察城市百态的社会窗口,街头赌博游戏摊前常聚集着寻求短暂刺激的劳动者。
天津市场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:老城周边及小刘庄工业区形成蔬菜集散地,西南角市场则融合布市与鱼市功能。每日清晨六点,绸缎布头的叫卖声与鱼贩的吆喝声交织,构成独特的市井晨曲。值得注意的是,鱼市交易中普遍存在的"短秤"现象(通常短缺一至二两),催生了顾客自带秤具的交易习惯,1936年的市场记录曾生动描绘顾客因争执分量而遗失钱物、小偷趁机行窃的典型场景。遍布市场的特色小吃摊,以锅巴菜、贴饽饽、炸糕等天津风味,成为工人们补充能量的重要选择,工厂周边摊位的热酒、咸花生等商品,更形成了具有职业特色的消费组合。
西广开"鬼市"作为天津最具特色的旧货交易中心,以拂晓前的交易时段和神秘氛围著称。这个被称为"喝破烂儿的"流动商贩聚集地,既是二手货流通枢纽,也是特殊时期的商品交易市场。1936年的市场调查显示,这里的交易品从虱子遍布的旧棉裤到精密的西洋钟表,涵盖生活物资与奢侈品。古董商与旧货贩子的交易在黎明时分达到高峰,至上午九点便消散无踪,这种昼伏夜出的经营模式,成为城市经济的特殊补充形态。
鬼市商品通过两类渠道流向城市各处:走街串巷的"喝破烂儿的"货郎承担着终端零售功能,同时为次日交易进行货源储备;西南角旧货市场则形成专业化交易场所,清代钱币与废铜烂铁共处一摊,旧书按斤售卖的现象折射出文化消费的底层生态。据地方文献记载,该市场的独特之处在于"原主交易"模式——失主常能在此发现失窃物品,而小偷与摊主通过"袖里吞金"(袖中议价)或春典暗语完成交易,这种隐秘的交易方式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商业奇观。
前奥租界的河边夜市构成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,五毛钱即可租用摊位与照明灯笼的低成本创业模式,吸引大量小商贩入驻。从袜子手绢等日用品到藤椅家具等耐用品,商品结构精准匹配工人消费能力,梅汤、油炸花生等应季食品更形成夜市独特的味觉记忆。
双重货币体系给工人生活带来显著影响:工厂工资以银元结算,而日常消费却需铜板,这种货币兑换环节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负担。遍布街巷的小钱铺虽提供兑换服务,但其价差波动常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,百米之内的兑换率差异迫使工人货比三家。季节因素更加剧兑换风险——春节前的铜板升值使银元购买力下降30%,而中秋前后的农产品上市又引发新一轮兑换波动,这种"收入贬值"现象直接影响工人家庭的节日消费。
为应对周期性资金短缺,当铺成为工人阶层的重要金融依赖。尽管月息高达15%且当期仅三个月,1947年的天津仍有44家正规当铺、千余家"小押店"及百余家旧货商店构成的信贷网络。"朝当暮赎"的短期周转模式(早晨当物换取现金,傍晚用当日收入赎回),反映出底层劳动者的生存智慧。春节前的典当高峰更形成特殊经济现象,据档案记载,工厂工人、搬运工和人力车夫构成典当主力,抵押物从衣物被褥到生产工具,涵盖生活与生产资料。
在有限的娱乐消费中,赌博活动呈现多样化形态。"摇会"作为流行赌戏,通过骰子数字竞猜吸引大量参与者;滚球游戏以铜板下注、糖果为彩头的低门槛模式,成为体力劳动者的休闲选择;织毯工人特别喜爱的骰子赌局,常以茶杯等生活用品为赌注,营造出"小赌怡情"的群体娱乐氛围。这些赌博形式虽简单粗糙,却在紧张劳作之余提供了必要的情绪释放出口。
南市"三不管"地区作为工人阶层的娱乐中心,以其多元业态和低廉消费成为休闲首选地。1935年的春节观察记录显示,这里聚集的"短衣小帽"群体中,工厂工人、学徒与苦力占比超七成。市场南区的旧衣交易、北区的日用杂货,配合流动剃头摊与代书先生的便民服务,构成功能完善的生活服务体系。
街头行医者构成"三不管"独特的文化景观:身着马褂长袍的"江湖郎中"常以"戒除鸦片""根治花柳病"为噱头;而杨宝亭式的卖药艺人则通过"警病医院院长"的虚假身份,以"铜鼓宣讲+强国叙事"的营销话术吸引顾客。与之竞争的武术卖艺者,则通过"先打赏后表演"的互动模式维持生计,这种"边演边讨"的经营策略成为底层艺人的生存智慧。
相对专业的服务型行当也在此聚集:修脚师专为劳动者解决足部劳损,"三步一摊"的拔牙摊满足基础医疗需求。1936年出现的"电动牙齿模型"表演,通过电池驱动的机械装置配合"心灵感应"的说辞,将拔牙服务包装成科技奇观;而"牛胎丸"作为苦力群体的"滋补圣品",其牛胎盘与蚂蚁成分的神秘配方,折射出底层劳动者的健康焦虑与养生智慧。
"三不管"北头的露天茶馆是民间艺术的重要展演空间:木偶摔跤表演通过一人双控的技艺展现民间智慧;"拉洋片"(又称"西洋景")以一个铜板八张图片的低廉价格,让工人接触到外国风景与历史故事。部分摊主更创新推出卓别林电影剪辑的"西洋镜",夜间则转向"肉感片子"的灰色经营,这种内容分级策略反映出文化消费的市场细分。
作为北方曲艺重镇,天津在二三十年代形成独特的艺术生态。南市燕乐、升平茶园既是艺人成长的摇篮,也是成名后的展演舞台;而"三不管"、谦德庄等工人聚集区的"撂地演出",则构成曲艺艺术的生存根基,这种"茶园+地摊"的双层市场结构,推动了曲艺形式的平民化发展。
"雨来散"苇棚戏院作为"三不管"的标志性建筑,以茅草屋顶的漏雨特性得名(谐音"雨伞")。这种简易剧场以长条木凳为座椅,高架木凳搭成舞台,几个铜板即可欣赏多场表演的亲民价格,使其成为工人文化消费的主要场所。
"蹦蹦戏"(评剧前身)在此创造了独特的经营模式:红底金字的剧目预告吸引观众,分段收费机制(每段1大枚铜板)适应工人的碎片化时间消费。女性观众享受"5大枚听半天"的优惠政策,而"每段一鼓"的收费信号(敲鼓提示付款),则形成灵活的消费结算方式。针对夜班工人的"上午场"与晚间常规演出的时间安排,使剧场利用率达到最大化,生意兴隆时每日可收入2000铜板,艺人与棚主按4:1比例分成的分配模式,反映出艺术生产的经济逻辑。
大鼓书作为主流表演形式,以其独特的艺术配置占据市场重要地位:架鼓(高至胸部)与弦乐伴奏的组合,配合女性艺人的韵文说唱,形成极具感染力的听觉体验。山东"梨花片"的铜片伴奏、京韵大鼓的满族民谣元素,共同构成多元的曲艺生态。值得注意的是,部分女艺人源自妓院"培养"的特殊背景,使其艺术生涯常伴随社会争议,而专业鼓书演员的身份转变,也成为她们摆脱屈辱命运的重要途径。
评书艺术在席棚茶馆中传承着历史记忆:老年说书人以"韵白相间"的讲述方式,将《三国》《水浒》等古典英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据观众回忆,说书人"唾沫飞溅仍全神贯注"的表演状态,与听众"身临其境"的沉浸体验,共同构成民间叙事传统的活态传承。
"落子馆"作为特殊娱乐场所,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功能:妓女群体以五六人为组的"时调"演唱,配合男性乐手伴奏,形成"窑调"表演特色。这种兼具娱乐与色情交易的双重属性,使其成为城市灰色经济的典型代表,也反映出女性在娱乐产业中的特殊生存状态。
相声艺术在此完成早期形态的孕育:三五人组合的表演形式中,"捧哏逗哏"的对话结构配合插科打诨的即兴发挥,形成独特的喜剧效果。据文献记载,这类表演"性暗示内容占比超六成",其通俗直白的表达风格深受底层男性欢迎,每段结束即收费的"现演现结"模式,也成为街头艺术的基本经营范式。
杂耍表演构成视觉娱乐的重要门类:"抖闷葫芦"的绳技表演展现精准控制;顶缸与踢毽子的技艺组合呈现肢体极限;而"什不闲儿"艺人的手脚并用乐器演奏,则创造出一人乐队的奇观效果。魔术表演中"丝毯变鱼缸"的经典桥段,配合武术表演的力量展示,共同构建起综合性的视觉盛宴。
工人聚集区的娱乐空间呈现出网络化分布特征:中心车站周边的"小营市场"作为"三不管"的微型翻版,其被火车浓烟笼罩的环境特征,与"婉转歌声+锣鼓喧阗"的感官体验形成强烈反差;谦德庄、河东区的同类娱乐区,则通过差异化定位满足区域工人需求,这种"一主多辅"的空间格局,使娱乐服务覆盖主要工业区。
曲艺形式的地域分野清晰反映移民文化构成:河南籍工人偏好河南坠子的乡音;山东移民钟情于梨花片的铁犁铧伴奏;河北农民出身的工人则最爱"蹦蹦戏"的乡土叙事。这种"籍贯-曲艺"的对应关系,使娱乐消费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,也推动了地方曲艺的跨区域传播。
至民国末期,民间艺术开始显现城市化转型迹象。京韵大鼓从"撂地长篇"向"茶园短段"的形式演变,伴奏乐器从单一鼓板发展为复杂乐队,这种艺术升级既适应城市娱乐的时间节奏,也提升了表演的专业水准。天津艺人创造的"二黄大鼓",在20年代形成独特艺术流派;而"鼓王"刘宝全创作的感恩主题新段子,则将传统伦理观念转化为符合城市审美趣味的艺术表达,这种文化创新预示着市民文化的兴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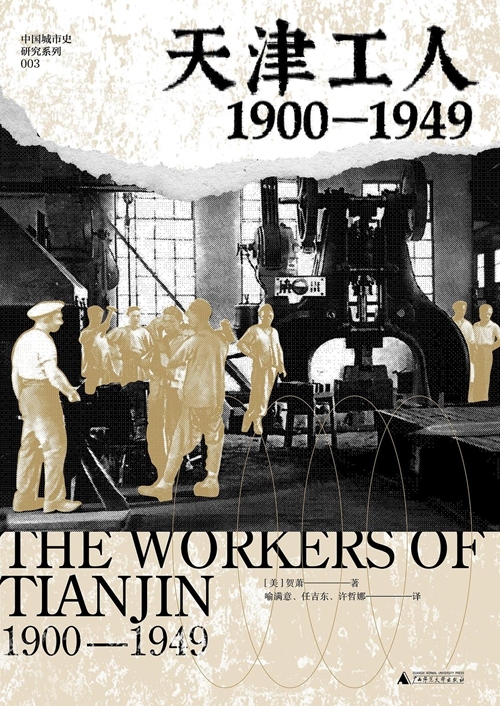
《天津工人:1900—1949》,[美]贺萧著,喻满意、任吉东、许哲娜译,大学问|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。
